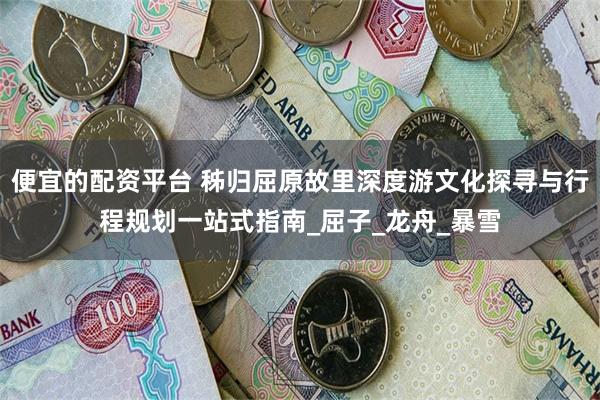杠杆炒股怎样快速
杠杆炒股怎样快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杠杆炒股怎样快速,作者:元淦恭,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4 年全国各地的经济数据陆续出炉。
广州的数据引人关注。2024 年,广州 GDP 实际增长 2.1%,名义增长 1.01%,在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敬陪末座,重庆也由此正式超过广州,成为 GDP "第四城"。
广州和京沪深的 GDP 差距显著拉大,深圳 GDP 比广州高出 5769 亿,深穗差距已经超过了穗苏(州)差距(4306 亿)。这样的 GDP 数字表现,无疑再度引发人们对于"广州还是不是一线城市"问题的讨论。
其实,广州 GDP 被重庆超过,这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要分析原因,主要是赛力斯的异军突起和广汽的颓势,让重庆和广州在汽车这两个支柱产业上此消彼长。但从长期来看,穗渝总量之争的实质仍然是东部发达城市和内陆中等省份之争。
去年我的分析大框架还是适用的,不过我没想到广州经济受地产和燃油车拖累如此之大,这么快就让出了 GDP "第四城"的宝座。但客观地说,论都会区的 GDP、影响力、辐射力,广州仍然远在重庆之上,广州作为中国"第四城"的地位并没有被撼动。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广州仍然稳居"一线城市"之列呢?
有论者认为,广州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然有着庞大的经济体量,是重要的国家门户、商业枢纽,当然还是"一线城市"。
但我们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一线城市"地位到底是不是规模决定的呢?
1990 年,深交所开始试营业,从那时起深圳就成为全国三大金融中心城市之一,整个九十年代,深圳都是炙手可热的"明星城市",但其实深圳 GDP 在 1999 年才跻身全国前四。
从 1999 年到 2012 年深圳 GDP 一直是全国第四,在这期间苏州、天津的 GDP 和深圳一度非常接近,甚至出现过一些季度甚至半年度超过深圳的情况,但也没有什么声音认为苏州和天津可以跻身"一线城市"和京沪穗深并列。
由是观之,经济规模当然是影响一个城市"线级"的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
什么是一线城市?在我看来,一线城市是经济高度发达、具有全国性资源配置能力,从而产生大量财富机会并吸引外来者广泛涌入的城市。符合这个条件的城市,即使 GDP 总量不排在前三前四,那也是一线城市,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城市,即使 GDP 排到了全国前三前四,也不是一线城市。
现在,广州在财富机会尤其是高薪工作机会上已经不能和京沪深相比较,但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可完全不是这样。
2000 年,上海和广州双双迈过了人均 GDP 达到 4000 美元的门槛,而当时北京的人均 GDP 才 2700 美元。这一年,北京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0350 元,上海的城镇人均收入是 11718 元,而广州的城镇人均收入是 13967 元。而这三个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是 15600 元、15439 元、18974 元。
广州无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均收入,还是以从业职工个人为标准的平均工资,都显著高于京沪。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当时广州跻身"一线城市",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涌入,可不是因为什么"大区中心的规模优势"、"坐拥两湖等人口大省腹地",就是因为广州的收入水平太高了(深圳当时的收入更高),高到北京上海都望尘莫及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
广东的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有港商、外资进入。彼时,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差距极大,香港的工厂到了广东,即使照香港的工资水平打一两折,那个工资水平对内地人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我去蛇口的改革开放纪念馆看当时蛇口一家纺织厂的工资条,1983 年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可以到 200 多元,那时候普通省会城市的工人工资才三四十元。
1988 年,宝洁进入中国,把中国区总部设在广州。跨国公司的薪酬水平本来就高,福利待遇极好,甚至还可以配发宝洁的股票,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宝洁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是没有对手的"第一 Offer "。
广州是外资、港资进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外资大大拉高了广州的收入水位,许多"打工人"发现在广州能赚钱,甚至赚大钱,纷纷涌入广州。产业和人口形成了正循环,又强化了广州的财政实力,反过来让广州的国企也更加强势,国企的工资也被带动起来。
与此同时,广州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动力,则源于商贸流通领域。1957 年,"广交会"开办,从那时起,广州就是封闭中国对外贸易的一扇窗口,而从 1978 年到 1992 年南方谈话期间,广州很大程度上继续在扮演这个窗口角色(因为广东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成规模开放)。
正是这种极其特殊的城市地位,让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到广州来的人,除了追逐外企的高薪,还有很多是做生意的草莽群体,"英雄不问出处",在广州各地批发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比比皆是。
经济发展起来了,广州还成为了中国重要的文化和传媒中心。
开放的环境、开明的气氛,成就了南方大院的传奇。
李海鹰、陈小奇、毛宁、杨钰莹、李春波等汇聚广州,让广州成为唱片业重镇。《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我不想说》、《小芳》…… 都是在广州唱响。
在经济影响力的加持之下,全国甚至掀起了学广东话的热潮。
那时的广州遍地黄金。每一个外来者到广州,都是为了获得成功。在这里,大家追逐财富,追逐名声,追逐影响力。无数人的野心,成就了广州。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广州后来的命运也在当时被注定。
相较其他省会城市,广州在吸引港资和外资这件事上,抢跑了十多年,所以广州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在"无竞争"条件下"保送"的。
广州从一开始就是外资进入中国内地的枢纽,这让广州在本质上是"买办"型的城市。来到广州的精英人群,大部分是冲着在广州打工挣高薪来的,广州的创业气氛其实一直并不算太浓厚。
从八十年代至今,在广州兴起的大型民营企业,与沿海同类城市相比算是很少的。全国工商联 2024 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以营收计)企业,杭州 38 家,深圳 27 家,无锡、苏州、宁波分别有 25 家、24 家、21 家,广州只有 7 家,就是例证。
广州发展得早,政府有钱,国企也发达了。这导致的结果是,广州其实早早就形成了国企、外企在高端就业市场上两分天下的格局,并没有民营企业什么事。
而广州民营经济最活跃的部分,其实就是依托商贸物流做生意的那一批。这个人群到现在也很富,但在这个群体中间,很难产生龙头企业、上市公司,整体上其实是非常"散装"的,他们自己发了财,也没办法提供多少高薪工作岗位出来。
有人说,广州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是因为它从商贸中心进阶起来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白天鹅宾馆建不建,宝洁、玛氏、安利、丰田来不来,和广州有没有批发市场压根没啥关系。广州的国企和外企,和海量的批发市场、中小微企业,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两个平行世界。
广州条件好,阔得早,它早早占据了许多庞大的赛道,譬如消费、地产、燃油车、石化。这些产业长期支撑了广州的 GDP 和财税,但广州也自然而然陷入了路径依赖。毕竟,广州是一艘大船,天然就很难掉头。
这些年来,广州经济面临挑战,广州社会的心气也不行了,涌向体制内追求稳定的越来越多。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广州的经济结构,无法提供足够多的高薪工作岗位,所以广州不再是一个遍地财富的地方了。
看看 2023 年主要城市的个税收入,上海 2383 亿,北京 1932 亿,深圳 1264 亿,杭州 624 亿,广州 491 亿。很多人说 GDP 数据不是原始数据,收入调查统计不靠谱,个税收入这个数据最真金白银,广州连深圳一半都没有了,杭州人口只有广州三分之二,但个税收入比广州高 27%,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20 世纪末的技术革命,把信息和资金流通的物理成本降到了零,导致金融和互联网两个行业无与伦比的劳动生产率。没有金融,没有互联网,没有科技产业,就很难有成规模的高薪岗位。
能不能当金融中心,中央说了算,地方政府主观努力意义不大,广州金融业不算发达,杭州、成都这些其他省会城市也一样。
但互联网和科技产业就不一样了,这完全是民营经济主导的领域。一个地方有没有民营经济的创业氛围,有没有科技创新的土壤,区别是很大的。
事实很清楚,在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广州不仅不能和京沪深相比,也早已被杭州抛离。
总部在广州的互联网公司,体量最大的也就一个唯品会。Shein 运营总部在番禺,但本质上其实做的是服装零售。网易理论上还注册在广州,但丁老板常年在杭州,不仅非游戏业务都在杭州,甚至连蛋仔派对这种现象级的游戏业务也在杭州,大家都已经当它是杭州公司了。Temu 一度把办公室设在番禺,到了 2023 年年底还是注册到深圳前海去了,去年已经人都搬去深圳了。
微信倒是在 T.I.T,说广州是互联网重镇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微信。但问题是微信是个非常轻、非常谦抑的 App,本身雇员数量就少,也不产生重运营的外部生态。微信在广州,也没法把广州互联网的氛围带起来。反观杭州有多少做直播、做 MCN、做代运营的,那是几十万人的生计。
新能源车,广汽有埃安,也有个小鹏,但这充其量只能算是拿到电车的"船票",谈不上多么突出。深圳比亚迪和杭州吉利作为大集团的整体优势,广州是很难追上的。
实际上,现在大厂在广州设分支机构的也不多。华为在广州的研究院,人数都未必有成都、杭州、西安这几个城市的多。至于互联网大厂,除了有历史渊源的腾讯网易,以及阿里收来的灵犀互娱,基本也没什么在广州的布局。反而是在杭州,抖音、快手、小红书的办公室全都开起来了,而且实际上都是承担全国性的业务功能,并不是区域分支。
最近,"杭州六小龙"(DeepSeek、游戏科学、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群核科技)火成了现象级。很多人发现,原来杭州真的不止有阿里啊,杭州的硬科技企业真是有后劲啊。我不知道这六家公司未来会怎样,但杭州能不断出新的牛逼的公司,绝对是必然。
广州和杭州其实不是一类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和广东巨大的先发优势,是很难用现在的眼光想象的,所以广州不需要有多少牛逼的本土民营企业,光是靠外企和国企,就可以"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杭州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特殊政策,也不是区域中心,国企相对弱,外企相对少,几十年来一路走到现在,全靠本土民营企业撑起经济一片天。机械有万向,石化有恒逸,快消有农夫,汽车有吉利,杭州大型民企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
杭州这座城市强烈的创业氛围和搞钱意识,广州是没有的。大家都知道,梁文锋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做 DeepSeek 的,他的幻方智能其实是做量化交易的,其实杭州做一级二级投资的人很多,搞钱的氛围和深圳是非常接近的。(当然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气氛)广州就不一样,似乎收租和饮茶才是正事。
数字不骗人。2023 年和 2020 年相比,杭州常住人口增长了 58.6 万人,成都增长了 46.52 万人,广州只增长了 27.97 万人,一个城市的财富机会少了,涌向这个城市的人自然就少了。
最近这些年,我个人有很直观的感受。深圳声势在往上走,杭州和成都的声势也在往上走,而广州的声势在往下走。大学同学聚会也好,朋友聚会也罢,在深圳的人越来越多,在广州的人越来越少。在广州的外地人,很多都搬去了杭州或者成都,住下来就"乐不思穗",甚至有些土生土长讲白话的广州人,跑到上海杭州之类的地方工作也不鲜见。
一个城市,需要有一个城市的标签。
比如杭州,它的标签就是民营经济、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量、民企 500 强企业数量、个税收入,这些硬核指标,杭州就是仅次于京沪深,杭州的创业氛围、高端就业在省会城市中就是最牛逼的。我现在身边还有在杭州创业的朋友,我在广州的朋友,除了一些做传媒的,其他人大都在体制内。
比如成都。很多人以为成都的标签是"西部省会""大区中心",好像这个城市也就是一个纯靠体量的城市,和广州是同一类型。成都和广州当然有许多相似性,但成都现在的标签比广州鲜明多了。
成都最重要的标签,就是消费和文娱。好像这两个标签也没那么独特,但细分析一下,就知道成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成都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消费主义的城市,老广那是出了名的穿人字拖吃大排档,成都人那就不一样了,豪车包包奢侈品我买故我在。
线下商业创新项目,第一看上海,第二看成都,已经是行业圈的共识。老牌的商场不说了,光是最近两年,成都的 Cosmo、SKP、麓湖 cpi、Regular、Cypark,就足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了。反观广州,最热闹的商业还是在天河北,除了前几年开的一个天环中心基本都还是老商场挑大梁,至于越秀荔湾老城的商业界面,更是一言难尽,谁逛谁知道。
成都也是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文创这件事,不容易像深圳、杭州的科创一样出大公司,但是这个行业里个体户也可以过得很好,小而美的公司也有空间,要是出个爆款更是事半功倍。"成都造"王者荣耀的长盛不衰自不必说,刚刚创下中国影史纪录的《哪吒》系列,也是成都可可豆公司出品的。
回到广州,现在专属广州的标签是什么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的标签就是"最发达、收入最高的城市",这是个极为清晰的定位。而现在,广州的标签是什么呢?当大家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牌的城市有底蕴"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难定义广州这座城市在一众省会城市中,除了体量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一骑绝尘的了。
在当下的省会城市里,杭州有创新力,成都有性价比,广州还能再方方面面对杭州、成都形成绝对优势吗?如果没有这种绝对优势,那还凭什么说广州要坐京沪深而不是杭州成都这一桌呢?
关于广州地位的相对下降,许多人经常讨论二级财政、三级财政的问题。首先,看城市要看结果,某种结果可能有客观原因,但是不影响我们对于这个结果本身的判断。
至于财政这个原因找得准不准,我就谈两点。第一,杭州是二级财政,但杭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成为民营经济第一城、数字经济第一城,那是靠政府财政砸出来的吗?那如果不是,杭州是二级财政还是三级财政是讨论杭州和广州经济生态谁更好的有效变量吗?
第二,有人说广州是三级财政深圳二级财政,广州吃亏了。你广州很多事是不能和深圳比(而且人家还是计划单列市),但是成都长沙合肥这一众明星城市也是三级财政啊,成都财政对中央和四川省也是净贡献啊(人口流入地一般都是财政净贡献人口流出地则相反,成都是人口流入地)。武汉和南京都是二级财政,这些年增长势头就比成都长沙合肥好吗?
在我看来,广州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众所周知,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城市作为中国最重要经济中心的地位,实际上是中央赋予,无可撼动的。它们享受的资源和政策都是长期性的。在这几个地方央国企强,外企也强,甚至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现在也很强,全能型选手没有什么短板。
杭州、成都这些其他省会城市,从中央的层面其实是没有额外给什么政策和资源的,就是要靠自己摸索闯出自己一条路来。
但是广州不一样,广州发展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中央要搞广东省这个改革开放试验田,所以它有十几年非常特殊的发展机遇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其实是和现在的京沪深一样,有特殊待遇的,游戏是开了外挂的。但等到全国的市场化改革铺开之后,京沪深和其他城市的"政策水位差"还在,但广州和其他城市的"政策水位差"突然消失了,原来的高级道具,突然没了。
广州凭借雄厚的基础,在这种水位差消失之后还打了很多年顺风仗,广州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未来焦虑,因为体量优势摆在这里。而杭州、成都这样的城市就不一样了,路都是自己摸出来的,只有切得足够准,足够刁,才能从先行者那里分到一杯羹。打顺风仗往往容易懈怠,打你封盘反而给人更多淬炼,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对一个城市而言,命运里所有的馈赠,也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作者:元淦恭